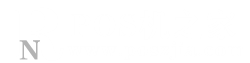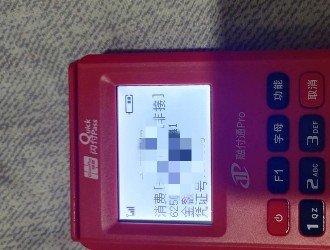網(wǎng)上有很多關(guān)于pos機(jī)運(yùn)行成本,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估算的知識(shí),也有很多人為大家解答關(guān)于pos機(jī)運(yùn)行成本的問(wèn)題,今天pos機(jī)之家(m.www690aa.com)為大家整理了關(guān)于這方面的知識(shí),讓我們一起來(lái)看下吧!
本文目錄一覽:
pos機(jī)運(yùn)行成本
■周莉萍 國(guó)家金融與發(fā)展實(shí)驗(yàn)室高級(jí)研究員
如何深刻理解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,從而準(zhǔn)確理解其估算口徑,合理估算其社會(huì)成本?本文從經(jīng)濟(jì)理論角度和研究角度梳理已有研究,追溯社會(huì)成本理論的理論淵源。重點(diǎn)回顧并借鑒以往研究對(duì)企業(yè)、支付工具等社會(huì)成本基本范疇的界定以及測(cè)算方法,總結(jié)理論上和國(guó)際上社會(huì)成本估算的通行做法,以更好地理解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及其估算。貨幣是一種公共產(chǎn)品,與貨幣職能相關(guān)的服務(wù)也屬于公共服務(wù)范疇。公共產(chǎn)品的供給必然產(chǎn)生一定的社會(huì)成本。當(dāng)前,我們?cè)谙硎茉絹?lái)越便利的支付服務(wù)時(shí),支付服務(wù)本身也對(duì)社會(huì)產(chǎn)生了一定的成本,耗費(fèi)了社會(huì)資源。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并不容易被消費(fèi)者直觀理解,因?yàn)槠渲饕嬖谟谥Ц懂a(chǎn)業(yè)鏈的供給主體。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分析兼具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意義和政策實(shí)踐意義。
一 理論視野中的社會(huì)成本
社會(huì)成本具有濃厚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意義,庇古和科斯開(kāi)創(chuàng)了社會(huì)成本的研究范式,使其成為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研究和法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研究的重要領(lǐng)域之一。本部分通過(guò)梳理以往的社會(huì)成本經(jīng)濟(jì)理論,界定本研究中社會(huì)成本的基本內(nèi)涵和外延,理清社會(huì)成本、私人成本的基本邊界。
? 庇古的觀點(diǎn)
庇古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研究的出發(fā)點(diǎn)和理論背景是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福利或者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效益。庇古構(gòu)建了基于邊際效用基數(shù)論的福利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,該理論體系有三個(gè)特征:以一定的價(jià)值判斷為出發(fā)點(diǎn),也就是根據(jù)已確定的社會(huì)目標(biāo),建立理論體系;以邊際效用基數(shù)論或邊際效用序數(shù)論為基礎(chǔ),建立福利概念;以社會(huì)目標(biāo)和福利理論為依據(jù),制定經(jīng)濟(jì)政策方案。舊福利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核心命題有兩個(gè):國(guó)民收入總量愈大,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福利就愈大;國(guó)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,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福利就愈大。他關(guān)注的是財(cái)富的積累即國(guó)民收入,因而任何增加或減損國(guó)民收入的社會(huì)成本都是他的社會(huì)成本研究?jī)?nèi)容。
在此理論背景下,庇古(1920)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的界定如下:一個(gè)人A在向另一人B提供某種有償服務(wù)時(shí),會(huì)附帶地向其他人(非同類服務(wù)的生產(chǎn)者)提供服務(wù)或給其他人造成損害,但卻無(wú)法從受益方獲取報(bào)酬,也無(wú)法對(duì)受害方給予補(bǔ)償。簡(jiǎn)而言之,社會(huì)成本是“列在消費(fèi)者與生產(chǎn)者賬目以外的,因?yàn)樯a(chǎn)與享用產(chǎn)品而令社會(huì)成員遭受的一切損失和不便”。對(duì)于社會(huì)成本,庇古的研究出發(fā)點(diǎn)是社會(huì)正外部性或負(fù)外部性,并提出了庇古稅等降低某種交易的社會(huì)成本的解決方法。但這一方法被后來(lái)的學(xué)者科斯證明并非最優(yōu)結(jié)果。
? 科斯的觀點(diǎn)
社會(huì)成本與社會(huì)總產(chǎn)值相對(duì)。科斯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問(wèn)題的論述源于其對(duì)社會(huì)總產(chǎn)值的研究。他曾提出,當(dāng)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在比較不同社會(huì)制度安排的優(yōu)劣時(shí),正確的方法是比較不同制度安排產(chǎn)生的社會(huì)總產(chǎn)值,而非私人總產(chǎn)值(Coase,1960)。這與庇古的社會(huì)福利出發(fā)點(diǎn)相似,科斯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問(wèn)題的研究也是源于其與庇古的學(xué)術(shù)辯論。
庇古是科斯的導(dǎo)師,二人曾就外部性和社會(huì)成本問(wèn)題進(jìn)行過(guò)精彩的辯論,內(nèi)容搜集在科斯的經(jīng)典論文《社會(huì)成本問(wèn)題(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)》中。在庇古處理社會(huì)外部性問(wèn)題的經(jīng)濟(jì)分析基礎(chǔ)上,科斯提出了不同分析思路,得出了不同的結(jié)論。核心辯論為:在面對(duì)A損害了B、產(chǎn)生外部性問(wèn)題時(shí),庇古的思路是如何阻止A,他提出阻止A有三種方法:一是A向B提供賠償;二是政府向A課稅;三是政府讓A停止工作。科斯認(rèn)為,社會(huì)外部性問(wèn)題正確的思考方式是:要使當(dāng)事人所遭受的損失都盡可能小,我們應(yīng)準(zhǔn)許A損害B,還是準(zhǔn)許B損害A,即應(yīng)該理清楚,A是否有權(quán)損害B,B是否有權(quán)要求A提供賠償。科斯最終的結(jié)論是,如果存在外部性,只要產(chǎn)權(quán)清晰,雙方也會(huì)通過(guò)合約找到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,制度安排的形式取決于它所能帶來(lái)的生產(chǎn)價(jià)值的增加是否大于其產(chǎn)生的交易成本。
科斯(Coase,1960)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問(wèn)題的分析闡釋,被后人總結(jié)為科斯定理。施蒂格勒最早將科斯的研究成果總結(jié)為科斯定理,核心內(nèi)容是“在完全競(jìng)爭(zhēng)條件下,私人成本和社會(huì)成本將會(huì)相等”。研讀科斯的《社會(huì)成本問(wèn)題》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科斯定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交易成本、社會(huì)成本、私人成本和產(chǎn)值最大化等。即如果交易成本為零且產(chǎn)權(quán)清晰界定,社會(huì)成本和私人成本會(huì)相等,產(chǎn)值能實(shí)現(xiàn)最大化。科斯所謂的社會(huì)成本本質(zhì)上是由社會(huì)所承擔(dān)的外部成本。社會(huì)成本為私人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和,在市場(chǎng)處于完全競(jìng)爭(zhēng)狀態(tài)時(shí),交易成本為零,此時(shí)私人成本等于社會(huì)成本。但現(xiàn)實(shí)世界中處處存在交易成本,私人成本與社會(huì)成本并不等同。后來(lái)的學(xué)者Williamson(1985)又將交易成本分為事前交易成本、事后交易成本和討價(jià)還價(jià)成本,總之是圍繞履行交易合同形成的相關(guān)費(fèi)用,產(chǎn)生的根本原因是不確定性、不信任或其他因素。
科斯的研究給出了社會(huì)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基本邏輯關(guān)系,即:
社會(huì)成本=私人成本+交易成本
或 外部成本=內(nèi)部成本+交易成本
上述等式給出了某一項(xiàng)經(jīng)濟(jì)活動(dòng)的社會(huì)成本為私人成本和外部性產(chǎn)生的交易成本之和。某一類活動(dòng)的社會(huì)成本等于所有參與此類活動(dòng)的個(gè)體的社會(huì)成本之和,但個(gè)體之間的交易成本可以相互抵消,進(jìn)而,總社會(huì)成本等于所有的個(gè)體的私人成本之和。這一思路也成為各國(guó)央行和本文估算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基本出發(fā)點(diǎn)。
? 社會(huì)學(xué)學(xué)者的觀點(diǎn):以蒂特馬斯為代表
社會(huì)學(xué)學(xué)者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的分析帶有獨(dú)特的學(xué)科特征和意義,其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范疇的界定較為寬泛,但核心理念與庇古和科斯一致。代表性觀點(diǎn)如蒂馬特斯(2011),他提出社會(huì)成本是“生產(chǎn)者沒(méi)有承擔(dān)生產(chǎn)貨品或提供服務(wù)的全部成本;而消費(fèi)者亦沒(méi)有承擔(dān)享用產(chǎn)品或服務(wù)的全部代價(jià)”。社會(huì)成本包括“由第三者或公眾所承受的一切因?yàn)樗饺说慕?jīng)濟(jì)和社會(huì)活動(dòng)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損失,這些社會(huì)性‘損害’可以反映在人類健康的損害上;可以表現(xiàn)為財(cái)產(chǎn)價(jià)值的破壞或衰退,以及天然財(cái)富的提前耗竭;此外,也可以表現(xiàn)為較不確實(shí)的價(jià)值損害”。這一觀點(diǎn)沒(méi)有脫離庇古和科斯提出的外部性、社會(huì)福利、社會(huì)成本等研究體系,是對(duì)外部性、交易成本的另一種闡釋。
? 小結(jié)
總體來(lái)看,以庇古和科斯為代表的20世紀(jì)的學(xué)者的研究奠定了社會(huì)成本基本理論,后人將社會(huì)成本問(wèn)題視為政府出臺(tái)相關(guān)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(jù),并在論證政策實(shí)踐中不斷發(fā)揚(yáng)光大。
在不完全競(jìng)爭(zhēng)條件下,社會(huì)成本包含交易成本或交易費(fèi)用,交易成本的存在意味著不同個(gè)體之間的交易摩擦,解決這種摩擦需要建立制度,交易成本是后來(lái)的制度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核心概念之一。顯然,科斯和威廉姆森研究中的社會(huì)成本必然包含交易成本。在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測(cè)算中,是否要考慮交易成本?零售支付體系和工具具有鮮明的雙邊市場(chǎng)特征,包括商業(yè)銀行和第三方支付平臺(tái)等為商家和消費(fèi)者構(gòu)建了雙邊選擇平臺(tái),二者通過(guò)外部性即交易費(fèi)用相互影響對(duì)方的選擇。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通常指的是支付服務(wù)相關(guān)主體耗費(fèi)的社會(huì)資源成本,強(qiáng)調(diào)支付服務(wù)相關(guān)主體與社會(huì)的關(guān)系,而不是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中各個(gè)主體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各支付主體在支付服務(wù)和環(huán)節(jié)中都付出了各種成本,包括相互之間支付的交易成本。因此,在計(jì)算個(gè)體參與支付交易的社會(huì)成本時(shí),應(yīng)該考慮交易成本;在計(jì)算某一類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以及所有支付工具的總社會(huì)成本時(shí),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中各主體之間的交易費(fèi)用被自動(dòng)抵消,此時(shí)總社會(huì)成本等于所有私人成本之和。
當(dāng)某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較高時(shí),政府應(yīng)該出臺(tái)政策阻止它的使用嗎?反之,當(dāng)某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較低時(shí),政府應(yīng)該出臺(tái)政策大力推動(dòng)它的使用嗎?這不是一個(gè)線性思維問(wèn)題。從理論的角度而言,不同的學(xué)者對(duì)這一類問(wèn)題早已作出了精辟的回答。從庇古到科斯,社會(huì)成本研究形成了較為清晰的研究范式,也成為我們理解和評(píng)估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個(gè)量化指標(biāo)、一種思路。按照庇古的觀點(diǎn),這種政策思路是正確的。按照科斯的觀點(diǎn),則是錯(cuò)誤的。科斯式的邏輯是,只要支付服務(wù)的產(chǎn)權(quán)足夠清晰,政府就無(wú)需干預(yù),支付服務(wù)產(chǎn)生的社會(huì)產(chǎn)值將達(dá)到最優(yōu),社會(huì)成本將最低。支付服務(wù)相互作用的個(gè)體之間將通過(guò)合約等方式達(dá)成最低交易費(fèi)用。科斯的邏輯支持各種支付工具創(chuàng)新探索;在支付工具發(fā)展較為穩(wěn)定時(shí),庇古的邏輯為支付政策提供了一種指導(dǎo)視角,將兩種理論運(yùn)用在支付工具不同的發(fā)展階段更為恰當(dāng)。
二 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測(cè)算:文獻(xiàn)回顧
討論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的社會(huì)成本對(duì)于支付行業(yè)未來(lái)發(fā)展有重要意義。支付功能作為貨幣的主要職能,在現(xiàn)代經(jīng)濟(jì)中充當(dāng)著“潤(rùn)滑劑”的角色,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高低直接從經(jīng)濟(jì)視角衡量著宏觀意義上的支付工具效率,也是政府和支付行業(yè)產(chǎn)品供給決策的基本依據(jù),有重要的政策實(shí)踐意義。下文主要回顧了學(xué)者、世界銀行和其他國(guó)家和地區(qū)的央行對(duì)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測(cè)算的基本文獻(xiàn),以求能從中找到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估算的一般思路和方法,對(duì)中國(guó)的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估算有所借鑒。
Humphrey and Berger(1990)最早嘗試研究支付工具的成本,并從成本角度比較不同的支付工具。他們對(duì)九種支付工具的私人成本和社會(huì)成本進(jìn)行了測(cè)算,發(fā)現(xiàn)現(xiàn)金的社會(huì)成本最低,其次是電子支付;若從私人成本角度來(lái)看,現(xiàn)金和支票的私人成本則最低。他們認(rèn)為,現(xiàn)實(shí)社會(huì)中付款人因?yàn)榭梢詮男庞每ê椭敝蝎@得浮動(dòng)收益,而且政府通常會(huì)在信用卡和支票市場(chǎng)失靈時(shí)干預(yù),導(dǎo)致他們常常過(guò)度使用這兩種支付工具。Humphrey et al.(1996)隨后又研究了14個(gè)發(fā)達(dá)國(guó)家的支付工具使用。認(rèn)為估算成本很難解釋人們選擇支付工具的行為,但支付的間接成本——犯罪率是一個(gè)很好的解釋變量,因此,支付工具的盜竊成本應(yīng)該被充分重視。Humphrey et al.(2003)研究認(rèn)為,從紙幣支付體系轉(zhuǎn)換為電子支付體系,能為一國(guó)節(jié)省1%的GDP。但后來(lái)的學(xué)者認(rèn)為他們的研究忽略了交易成本和社會(huì)收益,不夠嚴(yán)謹(jǐn)。Raa and Shestalova(2004)估計(jì)了現(xiàn)金和借記卡支付的固定成本和邊際社會(huì)成本,發(fā)現(xiàn)現(xiàn)金支付的固定交易成本低,適合用于小型交易,而借記卡支付的可變交易成本低,適合用于大型交易。他們估算的現(xiàn)金支付的盈虧平衡點(diǎn)是30歐元,如果考慮央行和商業(yè)銀行的現(xiàn)金補(bǔ)貼,則為13歐元。Pedersen (2012)估算丹麥的現(xiàn)金和Dankort卡的社會(huì)成本闕值為3.90歐元。Brits and Winder (2005)估算的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闕值則為11.63歐元(扣除消費(fèi)者成本)。Bergman et al.(2007)估算的借記卡的社會(huì)成本闕值為7.8歐元,信用卡為17.6歐元。
僅僅從成本視角來(lái)判斷一種支付工具的效率和未來(lái)政策制定,被廣為詬病,因此不少學(xué)者提出應(yīng)該從成本-收益兩種視角來(lái)研究某種支付工具,尤其是在提供支付工具的政策建議時(shí)。Stavins(1997)最早從成本-收益兩個(gè)視角研究支付工具,認(rèn)為電子支票支付能增加2.39%、總量約為14億美元的社會(huì)效益。加拿大央行的學(xué)者也從成本-收益視角分析了加拿大的支付工具使用情況,Swartz and Hahn(2006)基本的研究思路是,假設(shè)金融體系中原本沒(méi)有銀行卡和電子支付等工具,然后逐步引入這些工具,比較其增加的邊際成本,以及是否能給社會(huì)帶來(lái)更高的邊際收益。成本-收益視角的具體研究思路具體如下:一是估算一種新的支付工具的凈成本(邊際成本),并比較其與舊工具的凈成本;二是假設(shè)使用新支付工具的單位收益高于舊支付工具,估算相關(guān)期限內(nèi)社會(huì)凈收益的貼現(xiàn)現(xiàn)金流。最后,比較社會(huì)凈收益的貼現(xiàn)值和引入新支付工具的前端成本,為是否引入該新支付工具決策提供依據(jù)。根本思路是,考察引入一種新支付工具是否增加了社會(huì)福利。他們的研究考慮了支付工具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,社會(huì)成本和社會(huì)收益,但鑒于數(shù)據(jù)可得性,主要估算了社會(huì)成本和社會(huì)收益,私人成本和收益估算則使用了案例分析。研究的基本結(jié)論是:(1)現(xiàn)金和支票支付具有規(guī)模經(jīng)濟(jì)效應(yīng),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從中獲利;(2)電子支付體系、無(wú)現(xiàn)金社會(huì)能提高社會(huì)福利。
關(guān)于支付工具的私人成本和社會(huì)成本關(guān)系,不少學(xué)者從科斯的社會(huì)成本理論出發(fā),認(rèn)為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與私人成本對(duì)應(yīng),強(qiáng)調(diào)整個(gè)社會(huì)作為一個(gè)個(gè)體,指的是提供支付服務(wù)涉及到的各個(gè)主體所付出的社會(huì)資源成本(人力、資本和原材料成本)總和。他們認(rèn)為,支付工具的私人成本包括上述社會(huì)資源成本和交易費(fèi)用,交易費(fèi)用即用戶為使用支付工具付出的成本,例如付給支付平臺(tái)或機(jī)構(gòu)的使用費(fèi)用等私人成本,屬于個(gè)體之間的交易成本。交易成本應(yīng)該在社會(huì)成本中扣除(Hayashi and Keeton,2012)。
與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相關(guān)的數(shù)據(jù)很多是不公開(kāi)的、無(wú)法直接獲取的。意識(shí)到直接收集零售支付工具涉及的成本數(shù)據(jù)非常困難,或由于商業(yè)機(jī)密等約束,都加大了數(shù)據(jù)的搜尋難度。因此,必須一開(kāi)始就考慮數(shù)據(jù)來(lái)源、間接數(shù)據(jù)或替代性數(shù)據(jù)。有學(xué)者提出了一種思路,用現(xiàn)金的需求者、商業(yè)銀行、商家和消費(fèi)者支付的費(fèi)用即所有個(gè)體的私人成本作為社會(huì)成本估算口徑(Hayashi and Keeton,2012)。但私人成本也存在個(gè)體差異性,且機(jī)會(huì)成本不是貨幣成本,需要使用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等方式獲取抽樣樣本,用合適的方法進(jìn)行估算。各國(guó)央行和國(guó)際組織的相關(guān)研究大多也使用了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數(shù)據(jù),這些數(shù)據(jù)有很多是央行長(zhǎng)期積累的,有較強(qiáng)的說(shuō)服力,其研究方法和結(jié)果都值得借鑒。基于此,下文主要分析歐央行、世界銀行、挪威央行、澳大利亞央行、瑞典央行等對(duì)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的估算思路和方法等,以梳理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基本測(cè)算思路和路徑。
三 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測(cè)算:國(guó)際組織和部分央行的實(shí)踐
? 歐央行
歐央行(2012)早在2012年就估算了若干支付工具的私人成本和社會(huì)成本。歐央行認(rèn)為,社會(huì)成本是支付工具服務(wù)的社會(huì)資源成本。因私人成本往往對(duì)應(yīng)另一主體的私人收益,簡(jiǎn)單加總所有的支付工具私人成本得到的社會(huì)成本往往是被高估的。但是,歐央行也指出,沒(méi)有考慮支付服務(wù)需求方的成本,主要原因是數(shù)據(jù)獲得難度太高。
歐央行對(duì)支付工具成本的基本分析框架如下:
表1 歐央行: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分析框架
資料來(lái)源:ECB(2012)。
表2 零售支付工具私人成本和社會(huì)成本估算
資料來(lái)源:ECB(2012)。
1. 測(cè)算思路
上述表1和表2是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意義上的社會(huì)成本。表2表明:
零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=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所有參與主體的內(nèi)部成本
總社會(huì)成本=所有零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
為了得到某一類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,歐央行假定商業(yè)銀行是主要的支付服務(wù)供應(yīng)商,商業(yè)銀行同時(shí)提供現(xiàn)金、銀行卡和電子支付服務(wù)。以商業(yè)銀行為核心,歐央行又將支付服務(wù)參與主體的內(nèi)部成本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,通過(guò)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的方式,測(cè)算每一個(gè)主體在每一種支付工具(現(xiàn)金、借記卡、信用卡、電子支付)上付出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,最后加總得出每一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。
2. 測(cè)算方法
在實(shí)際測(cè)算中,歐央行采用了基于活動(dòng)的測(cè)算法(activity based costs,簡(jiǎn)稱ABC)和基于資源的成本測(cè)算法。歐央行測(cè)算的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主體范圍僅僅包括提供支付工具和服務(wù)相關(guān)主體,包括中央銀行、商業(yè)銀行和銀行間基礎(chǔ)設(shè)施供應(yīng)商、零售商和企業(yè)、運(yùn)鈔公司等。主要測(cè)算途徑是向上述主體發(fā)放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。
除了上述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,支付相關(guān)數(shù)據(jù)主要來(lái)自歐央行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。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可以估算每一種支付工具每歐元的社會(huì)成本,以及每一種支付工具每一筆交易的社會(huì)成本。歐央行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可以提供全社會(huì)支付總量、支付總值以及支付結(jié)構(gòu)(總交易量和總交易值)。綜合起來(lái),可以估算出每一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和所有零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。
歐央行最終的測(cè)算結(jié)果如下:歐洲地區(qū)13個(gè)參與國(guó)的零售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約為450億歐元,占GDP的0.96%。當(dāng)測(cè)算范圍擴(kuò)大至27個(gè)歐盟成員國(guó)時(shí),零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約為1300億歐元,占GDP的1%。在總的社會(huì)成本中,商業(yè)銀行和金融基礎(chǔ)設(shè)施的社會(huì)成本占50%,零售商的社會(huì)成本占46%,中央銀行和中介公司的社會(huì)成本分別占比3%和1%。從支付工具維度來(lái)看,與現(xiàn)金有關(guān)的社會(huì)成本占總社會(huì)陳本約50%,但每一筆現(xiàn)金交易產(chǎn)生的社會(huì)成本是最低的,低于銀行卡單筆社會(huì)成本。在歐盟近三分之二的國(guó)家里,借記卡支付比現(xiàn)金支付的單筆社會(huì)成本低(ECB,2012)。
? 世界銀行
世界銀行借鑒了歐央行的部分觀點(diǎn),設(shè)計(jì)了零售支付工具的成本測(cè)算框架,供各國(guó)央行和其他機(jī)構(gòu)、個(gè)人參考。世行認(rèn)為從高社會(huì)成本的支付工具轉(zhuǎn)向低社會(huì)成本的工具有利于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,肯定了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對(duì)于支付工具發(fā)展決策的重要指導(dǎo)作用,也指出了較低的社會(huì)成本意味著支付工具的普惠性會(huì)更強(qiáng),從而間接推動(dòng)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(Worldbank,2016)。世行曾在2015年以前對(duì)零售支付工具成本的研究進(jìn)行了梳理,區(qū)分了不同文章研究的支付工具成本的性質(zhì)及涉及的機(jī)構(gòu)等,包括平均成本、邊際成本、總資源成本等。其中,總資源成本即社會(huì)成本。世界銀行認(rèn)為,整個(gè)經(jīng)濟(jì)體系中的零售支付工具成本包括支付服務(wù)的供給、需求雙方產(chǎn)生的內(nèi)部資源成本總和。世行排除了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中多個(gè)主體之間的轉(zhuǎn)移成本(transfer costs),社會(huì)成本(總資源成本)的統(tǒng)計(jì)范疇如下表3。
表3 世界銀行:零售支付工具的資源成本、轉(zhuǎn)移成本及總成本的關(guān)系
資料來(lái)源:Word Bank(2016)。
支付工具涉及的資源成本包括哪些?世界銀行的學(xué)者進(jìn)一步給出明細(xì)內(nèi)容,見(jiàn)表4:
表4 世界銀行:支付工具的資源成本類型
資料來(lái)源:Word Bank(2016)。
表4涉及的絕大多數(shù)成本都需要通過(guò)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等方式,從消費(fèi)者處獲取。每一種支付工具的成本基本被涵蓋在表4中,但又有自身特殊的成本類型。具體而言,不同支付工具的使用者面臨的具體成本內(nèi)容如下表5和表6:
表5 世界銀行:各種支付工具的成本-付款人視角
資料來(lái)源:Word Bank(2016)。
表6 世界銀行:各種支付工具的成本-收款人視角
資料來(lái)源:Word Bank(2016)。
上述從支付服務(wù)的供給方和需求方、從資源成本視角考量的社會(huì)成本具有鮮明的個(gè)體特征,與歐央行的思路有較大區(qū)別。因?yàn)樯鐣?huì)資源涵蓋了所有主體,包括支付服務(wù)的需求方所付出的資源,比單純的支付服務(wù)供給、生產(chǎn)范圍更加寬泛。總體來(lái)看,世界銀行關(guān)于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測(cè)算的基本思路是,支付工具供給方和需求方的總資源成本即為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。而且,這里的“資源”包含人力資源、各種設(shè)備材料、資金等。但人力資源被分成了多種時(shí)間成本,圍繞著與支付服務(wù)供給、需求有關(guān)的時(shí)間成本。在數(shù)據(jù)來(lái)源方面,由于每一個(gè)個(gè)體所耗費(fèi)的資源成本差異較大,世界銀行的社會(huì)成本估算數(shù)據(jù)基本都需要通過(guò)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的方式獲取平均估值,與歐央行思路一致。
? 其他央行實(shí)踐
1. 澳大利亞儲(chǔ)備銀行
澳大利亞儲(chǔ)備銀行的學(xué)者們測(cè)算了每種支付工具在長(zhǎng)期增加的資源成本,基本思路是圍繞提供支付服務(wù)的銀行賬戶測(cè)算相關(guān)成本。但是,長(zhǎng)期增量資源成本的測(cè)算比較困難,最終,他們選取了平均成本來(lái)作為替代指標(biāo)。測(cè)算的結(jié)果是,金融機(jī)構(gòu)和支付企業(yè)每年為個(gè)人提供支付服務(wù)付出的成本至少有85億美元,約占GDP的0.8%。其中,現(xiàn)金支付的成本為總成本的一半,原因是澳大利亞個(gè)人支付總量中有三分之一是使用現(xiàn)金。他們?cè)跍y(cè)算中考慮了便利支付所付出的成本,這部分成本約占總支付成本的四分之一(Schwartz, Fabo, Bailey and Carter,2007)。
圍繞銀行賬戶、支付賬戶估算的支付平均成本基本范疇。在具體估算是,澳大利亞央行將支付工具的成本分為三部分:第一部分是金融機(jī)構(gòu)或支付平臺(tái)設(shè)立和維護(hù)銀行賬戶等支付賬戶的成本;第二部分是直接支付成本;除了直接成本外,澳大利亞央行認(rèn)為金融機(jī)構(gòu)或支付平臺(tái)還為每一種支付工具付出了營(yíng)運(yùn)成本(merchant cost)。
可以看出,澳大利亞央行的測(cè)算方法與歐央行有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。相同之處是,二者均從支付服務(wù)的供給視角測(cè)算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,二者與世界銀行不同,后者是從支付服務(wù)的供給和需求雙方來(lái)測(cè)算總社會(huì)成本。當(dāng)然,世界銀行給出的只是基本測(cè)算思路和框架指導(dǎo),沒(méi)有具體實(shí)踐。在實(shí)踐中,多家央行之所以不考慮支付需求方的成本,主要原因是數(shù)據(jù)難以獲取。
澳大利亞央行和歐央行最明顯的不同之處是,歐央行將商業(yè)銀行的營(yíng)運(yùn)成本視為所有支付工具的直接成本、間接成本和其他成本之和,澳大利亞央行則認(rèn)為支付服務(wù)的直接成本在商業(yè)銀行營(yíng)運(yùn)成本之外。
2. 挪威央行
挪威央行估算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的思路與歐央行相同,二者都遵循“活動(dòng)導(dǎo)向型(簡(jiǎn)稱ABC)”而不是資源導(dǎo)向型思路,即基于與提供支付服務(wù)相關(guān)所有直接和間接支持活動(dòng)來(lái)估算社會(huì)成本。但挪威央行的研究早于歐央行(ECB,2012)的研究。
挪威央行對(duì)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定義是“行業(yè)產(chǎn)出生產(chǎn)過(guò)程中對(duì)資源的實(shí)際使用”。挪威央行比較推崇從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角度衡量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。通過(guò)統(tǒng)計(jì)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中所有代理人的生產(chǎn)成本估算出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,代理人包括商業(yè)銀行、中央銀行、商家、分包商和用戶等(Gresvik and Harre,2009)。關(guān)于與支付有關(guān)的基礎(chǔ)設(shè)施,例如用戶的電腦或智能手機(jī)、寬帶、郵政服務(wù)等,甚至道路、橋梁,這些廣義的支付基礎(chǔ)設(shè)施,挪威央行認(rèn)為不應(yīng)計(jì)入社會(huì)成本,理由是這些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并不單單是為了服務(wù)支付交易,也很難從中區(qū)分出或者分?jǐn)偝鲋Ц斗?wù)相關(guān)的折舊成本。其他央行的測(cè)算也基本遵循了這一觀點(diǎn),不考慮廣義的支付基礎(chǔ)設(shè)施。歐央行考慮了銀行間支持資金流動(dòng)的金融基礎(chǔ)設(shè)施。
在私人成本和社會(huì)成本的關(guān)系上,挪威央行認(rèn)為,私人成本是代理人的全部成本,包括生產(chǎn)成本和支付的費(fèi)用,例如商業(yè)銀行向分包商支付的與用戶支付服務(wù)相關(guān)的費(fèi)用。私人成本扣除支付的費(fèi)用之后是凈私人成本,如果為正,證明其有損失。同時(shí),還存在鑄幣稅成本,即持有現(xiàn)金的機(jī)會(huì)成本,通常用持有存款的利息來(lái)估算。社會(huì)成本不是所有的私人成本的加總,而是需要扣除代理人之間相互支付的費(fèi)用。挪威央行強(qiáng)調(diào),其估算的是平均成本而不是邊際成本。
每種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具體估算思路和方法如下:
表7 挪威央行: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估算方法
資料來(lái)源:Gresvik and Harre(2009)。
挪威央行對(duì)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估算的基本結(jié)果是:在2007年,挪威支付體系的社會(huì)成本為111.6億克朗,約占GDP的0.49%。其中,現(xiàn)金支付的社會(huì)成本是34.9億克朗,銀行卡支付的社會(huì)成本是53.6億克朗,銀行轉(zhuǎn)賬支付的社會(huì)成本是23.1億克朗,分別占社會(huì)總成本的31.3%,48%,20.7%。從代理人角度來(lái)看,商業(yè)銀行的支付社會(huì)成本為49.5億克朗,挪威央行為1.3億克朗,用戶為21.8億克朗,商家和其他機(jī)構(gòu)為1.53億克朗,分包商為23.7億克朗。
3. 瑞典央行
瑞典央行曾對(duì)本國(guó)支付工具在2009年的社會(huì)成本和私人成本進(jìn)行過(guò)估算(Segendorf and Jansson,2012)。大致思路是將社會(huì)成本區(qū)分為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,分別估算中央銀行、商業(yè)銀行、零售商、消費(fèi)者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,得出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的社會(huì)成本。對(duì)于每種支付工具的可變成本,瑞典央行將其簡(jiǎn)化為時(shí)間成本,并將時(shí)間成本簡(jiǎn)化為交易值的方程。其中,現(xiàn)金的時(shí)間成本與交易值呈線性關(guān)系,借記卡的時(shí)間成本則與交易值大小無(wú)關(guān)。具體估算思路和方法見(jiàn)表8。
表8 瑞典央行:支付工具的私人成本和社會(huì)成本關(guān)系
資料來(lái)源:Segendorf and Jansson(2012)。
瑞典央行的總體方法是: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等于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中所有相關(guān)主體,包括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凈私人成本之和,或者說(shuō)生產(chǎn)成本之和。瑞典央行所謂的支付工具生產(chǎn)成本涵蓋了公眾,這在邏輯上有不妥之處,因?yàn)楣娛侵Ц斗?wù)的需求方,從產(chǎn)出的一般意義上來(lái)講,其并沒(méi)有參與生產(chǎn),不存在生產(chǎn)成本。
瑞典央行最終的估算結(jié)果是支付體系社會(huì)成本約占GDP的0.68%。其中,現(xiàn)金、借記卡和信用卡的社會(huì)成本占GDP比重分別為0.26%,0.19%和0.09%。而且現(xiàn)金的社會(huì)成本比借記卡低1.88歐元,比信用卡支付低42.37歐元,即瑞典的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從高到低分別為信用卡、現(xiàn)金和借記卡,且各類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結(jié)構(gòu)差異較大。瑞典央行認(rèn)為,用戶最優(yōu)支付工具選擇主要取決于交易規(guī)模大小。
4. 荷蘭央行
荷蘭央行早在2005年就測(cè)算了本國(guó)支付體系的社會(huì)成本。在社會(huì)成本測(cè)算方面,荷蘭央行主要測(cè)算了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和社會(huì)收益,以及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。
在估算社會(huì)成本時(shí),荷蘭央行主要考慮了中央銀行、財(cái)政部鑄幣部門、商業(yè)銀行和零售部門的社會(huì)成本,沒(méi)有考慮用戶在支付時(shí)耗費(fèi)的時(shí)間成本等。關(guān)于鑄幣稅,荷蘭央行認(rèn)為在測(cè)算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時(shí)應(yīng)該考慮,是商業(yè)銀行、商家和用戶等現(xiàn)金持有者對(duì)中央銀行的隱性收益轉(zhuǎn)移,因?yàn)橹醒脬y行發(fā)行的現(xiàn)金是債務(wù)性質(zhì),但央行從不為其負(fù)債支付利息,反過(guò)來(lái),持有現(xiàn)金的機(jī)會(huì)成本即是鑄幣稅。在估算時(shí)間上,荷蘭央行選取了3-5年的數(shù)據(jù),目的是考察可變成本的演變特征。基本的測(cè)算思路就是,考察特定支付工具服務(wù)過(guò)程中,上述機(jī)構(gòu)的固定成本,與交易相關(guān)的可變成本以及與銷售相關(guān)的可變成本,加總每一個(gè)部門的社會(huì)成本,得出特定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。
數(shù)據(jù)獲取和問(wèn)卷設(shè)計(jì)。關(guān)于每一個(gè)部門在每一種支付工具上付出的成本,荷蘭銀行采用了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方式,評(píng)估每個(gè)部門在每種支付工具上付出的成本類型以及成本比例。以商業(yè)銀行為例。
荷蘭央行的研究結(jié)論主要如下:包括POS支付在內(nèi)的支付體系社會(huì)成本約為每筆交易0.35歐元,總社會(huì)成本約占GDP的0.65%,總支付成本占總交易值得比重為2.4%,符合他們的基本觀念即“支付體系從來(lái)都沒(méi)有免費(fèi)的午餐”(Brits and Winder,2005)。在支付工具內(nèi)部結(jié)構(gòu)方面,他們發(fā)現(xiàn)電子錢包的成本最低;每一個(gè)家庭每年的支付社會(huì)成本超過(guò)400歐元;對(duì)于低于0.63歐元的交易而言,現(xiàn)金比借記卡更為經(jīng)濟(jì);從成本的角度而言,最不適合作為支付工具的是信用卡;使用公共資源為央行的現(xiàn)金流通埋單造成的扭曲效應(yīng)有限。他們還認(rèn)為,一個(gè)少量使用現(xiàn)金支付的社會(huì)比一個(gè)無(wú)現(xiàn)金社會(huì)好,至少?gòu)闹衅趤?lái)看如此。
5. 丹麥央行
丹麥央行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:估算用戶、零售商和商業(yè)銀行等支付服務(wù)參與主體、需求者等付出的總成本,剔除不同主體之間的費(fèi)用,得到社會(huì)成本。同時(shí),又將社會(huì)成本分為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。即
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=總成本-主體之間的費(fèi)用=固定成本+可變成本
丹麥央行(Danmrks Nationalbank,2012)的研究結(jié)果表明,在2009年,丹麥支付體系的總成本約為90億丹麥克朗;對(duì)于小額支付而言,現(xiàn)金的支付成本最低,但對(duì)于超過(guò)29丹麥克朗的支付來(lái)說(shuō),Dankort支付成本最低;在一般情況下,信用卡的支付成本高于Dankort;允許零售商向所有類型的信用卡支付收費(fèi),將降低其社會(huì)成本。
四 結(jié)論和啟示
前文分析全面回顧了與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相關(guān)的理論和測(cè)算實(shí)踐經(jīng)驗(yàn),核心結(jié)論如下:
一是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估算方法。顯而易見(jiàn),不同的估算方法最終得到的結(jié)果差異較大。而關(guān)于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估算方法,大致可以分為兩類:一類是成本-收益法,估算與支付主要相關(guān)的機(jī)構(gòu)(中央銀行、商業(yè)銀行、零售商、基礎(chǔ)設(shè)施供應(yīng)商、消費(fèi)者即用戶)的成本和收益,得出凈成本。支付工具的類別大致包括現(xiàn)金、借記卡、信用卡,支票和電子貨幣等。代表性研究包括比利時(shí)央行(Banque Nationale de Belgique,2005),Bergman et al.(2007),Brits and Winder(2005),丹麥央行(Danmarks Nationalbank,2012), Guibourg and Segendorf(2007)and Turján et al.(2011)。這類方法不僅僅測(cè)算另外支付工具的總社會(huì)成本,還考慮了支付工具的凈社會(huì)成本、邊際成本。第二類研究是僅僅考慮支付服務(wù)的社會(huì)成本,不考慮社會(huì)收益,這類方法考慮的是總社會(huì)成本、平均成本。又分為兩類方法:一是活動(dòng)導(dǎo)向型成本估算法(即ABC),將分布于不同支付工具和服務(wù)的成本集中估算在商業(yè)銀行等服務(wù)主體上,根據(jù)不同支付工具交易量和結(jié)構(gòu)對(duì)單一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進(jìn)行估算。這類研究通常將支付分為直接借記支付和信用卡轉(zhuǎn)賬支付。代表性研究包括葡萄牙央行的研究(Banco de Portugal,2007)和挪威央行的研究(Gresvik and Owre,2003;Gresvik and Haare,2009)。二是資源導(dǎo)向型成本估算法(即RBC),對(duì)支付服務(wù)的供給和需求雙方投入的社會(huì)資源進(jìn)行估算。該方法與科斯關(guān)于社會(huì)成本的估算一脈相承,邏輯較為一致。
總體來(lái)看,兩種測(cè)算方法的核心理念均來(lái)自科斯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論述,在加總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各主體私人成本時(shí)剔除了各主體之間的交易費(fèi)用,認(rèn)為社會(huì)成本等于各主體內(nèi)部成本之和。只不過(guò)在數(shù)據(jù)可得的情況下,個(gè)別央行額外估算了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收益,從而估算了支付工具的凈成本、邊際成本,為決策者提供了更為客觀和全面的論據(jù)。
表9 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估算思路和方法歸類
資料來(lái)源:作者總結(jié)。
在成本估算方法上,各大央行通常又將社會(huì)成本區(qū)分為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,分別估算每種支付工具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,從而在估算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同時(shí),探討支付工具演進(jìn)的內(nèi)在規(guī)律,例如規(guī)模經(jīng)濟(jì)、邊際成本等。總體來(lái)看,各國(guó)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結(jié)構(gòu)呈現(xiàn)一定的規(guī)律,如現(xiàn)金的社會(huì)成本中可變成本較高,而非現(xiàn)金支付(包括銀行卡、信用轉(zhuǎn)賬、移動(dòng)支付、電子錢包等)社會(huì)成本中的固定成本較高。澳大利亞央行、挪威央行、荷蘭央行和比利時(shí)央行均估算了整個(gè)支付體系社會(huì)成本中的固定成本(與支付基礎(chǔ)設(shè)施有關(guān)的)和可變的資源成本,以及每一筆支付交易的社會(huì)成本、每單位支付交易的社會(huì)成本。
二是數(shù)據(jù)來(lái)源。幾乎所有央行都是利用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數(shù)據(jù)進(jìn)行了估算。各大央行估算的支付工具范疇包括現(xiàn)金、借記卡、信用卡、預(yù)付卡、直接借記卡、直接貸記卡、支票、銀行轉(zhuǎn)賬、POS等,與這些支付工具相關(guān)的成本呈現(xiàn)多樣化和高度復(fù)雜特征,有很多不是客觀的、可貨幣化的,而是主觀的、個(gè)性化的、非貨幣化的,很難估算。除了不斷簡(jiǎn)化,例如將所有的成本簡(jiǎn)化為時(shí)間成本等,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是獲取此類數(shù)據(jù)的主要方式。在調(diào)查問(wèn)卷設(shè)計(jì)上,幾大央行使用的問(wèn)卷均包含商業(yè)銀行、商家和個(gè)人用戶等,也有央行向支付服務(wù)分包商以及支付指令搜集機(jī)構(gòu)、收單機(jī)構(gòu)等等發(fā)出了問(wèn)卷,如澳大利亞央行和挪威央行。問(wèn)卷的內(nèi)容主要集中在支付服務(wù)時(shí)間以及其他不變成本和可變成本等。
三是估算結(jié)果比較。綜合來(lái)看,幾大央行對(duì)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估算結(jié)果概況見(jiàn)表10、表11、表12和表13。
表10 幾大央行對(duì)支付工具社會(huì)成本的估算結(jié)果
資料來(lái)源:Gresvik and Harre(2009),Kari and Viren(2008)。
表11 各大央行估算的單位支付的社會(huì)成本(1美元)
資料來(lái)源:Hayashi and Keeton(2012)。
表12 支付工具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的分?jǐn)偙壤?/strong>
資料來(lái)源:Gresvik and Harre(2009)。
表13 各代理人對(duì)社會(huì)成本的分?jǐn)偙壤?/strong>
資料來(lái)源:Gresvik and Harre(2009)。
總體來(lái)看,支付工具的總社會(huì)成本占GDP的比例均低于1%,最低的瑞典僅占GDP的0.4%。當(dāng)然,原因可能是瑞典央行的估算工具范圍過(guò)于狹窄,僅僅包括了現(xiàn)金和銀行卡。已有的研究基本來(lái)自各國(guó)央行,僅僅是個(gè)性化地、對(duì)本國(guó)支付工具的大致估算,具體的估算口徑、方法和標(biāo)準(zhǔn)都不統(tǒng)一。目前,還沒(méi)有研究對(duì)所有國(guó)家和地區(qū)的支付工具,按統(tǒng)一標(biāo)準(zhǔn)進(jìn)行估算。所以,橫向比較各國(guó)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還不具有實(shí)踐意義,當(dāng)前各央行的估算結(jié)果僅僅可以用于評(píng)估本國(guó)國(guó)內(nèi)支付工具,不具有推廣意義。
另外,從結(jié)果還可以看出部分央行的估算結(jié)果與其本國(guó)實(shí)踐也存在一定的差距。社會(huì)成本估算的結(jié)果與人們?cè)趯?shí)踐中選擇的支付工具并不是一一對(duì)稱,這一點(diǎn)也充分體現(xiàn)了個(gè)體支付行為的外部性特征。例如,瑞典央行發(fā)現(xiàn),用戶支付行為與估算的社會(huì)成本意義上的最優(yōu)支付選擇并不一致。例如,很多用戶在大額支付時(shí)經(jīng)常用現(xiàn)金而不是銀行卡;女性的支付工具選擇與他們的經(jīng)濟(jì)動(dòng)機(jī)并不一致,而男性并不存在這種問(wèn)題(Segendorf and Jansson,2012)。對(duì)于這一點(diǎn),我們的理解來(lái)自兩個(gè)維度:(1)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意義的理解是,支付工具定價(jià)沒(méi)有充分反映社會(huì)成本;非現(xiàn)金支付工具定價(jià)存在一定的扭曲或者不合理的政策,有進(jìn)一步改進(jìn)的空間;現(xiàn)金具有典型的公共產(chǎn)品性質(zhì),無(wú)法完全體現(xiàn)為私人成本。(2)從非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因素來(lái)看,影響支付工具選擇的主要因素不僅僅包括社會(huì)成本、私人成本,還包括個(gè)人偏好、支付效率、支付安全、支付政策或制度等其他多種綜合因素。簡(jiǎn)而言之,社會(huì)成本指標(biāo)是評(píng)估一種支付工具經(jīng)濟(jì)效率的直接指標(biāo),但不是最全面的評(píng)估指標(biāo)。
最后,各國(guó)對(duì)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的主體范疇以及社會(huì)成本相關(guān)的私人成本范疇估算還存在差異,核心問(wèn)題可以歸結(jié)為哪些主體的私人成本被計(jì)入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?差異之處具體體現(xiàn)在兩方面:(1)支付相關(guān)的清算基礎(chǔ)設(shè)施機(jī)構(gòu)的私人成本是否計(jì)入?大部分央行并不計(jì)入其中,世界銀行、歐央行及少許央行將其私人成本計(jì)入其中;清算機(jī)構(gòu)屬于廣義的支付產(chǎn)業(yè)鏈的主體,屬于支付服務(wù)的間接主體,而非直接主體,為商業(yè)銀行最終完成支付服務(wù)提供清算便利。但因其為所有的支付工具服務(wù),在估算所有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時(shí)可以考慮,但具體到單一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測(cè)算時(shí),并不容易從中區(qū)分出具體的成本。這兩點(diǎn)可能是多數(shù)央行不考慮清算基礎(chǔ)設(shè)施成本的主要原因。(2)支付服務(wù)用戶的私人成本是否計(jì)入其中,世行給出的測(cè)算框架中包括用戶成本,歐央行認(rèn)可但認(rèn)為限于數(shù)據(jù)獲取難度過(guò)大,總體成本不高可以忽略不計(jì),多數(shù)央行并不考慮用戶的私人成本。澳大利亞央行和挪威央行同時(shí)估算了支付工具的私人成本,但比利時(shí)和荷蘭央行沒(méi)有估算此項(xiàng)。從估算支付服務(wù)的供給方——中央銀行、商業(yè)銀行、分包服務(wù)商等機(jī)構(gòu)的資源耗費(fèi)成本測(cè)算社會(huì)成本,這種思路有效區(qū)分了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和私人成本,在理論上沒(méi)有瑕疵。但依然沒(méi)有理清一個(gè)問(wèn)題,即社會(huì)資源的范疇如何確定。個(gè)人用戶付出的私人成本耗費(fèi)了社會(huì)資源,是否也應(yīng)該計(jì)入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?這些問(wèn)題有待進(jìn)一步思考。
(本文來(lái)源于《中國(guó)支付清算》2021年第1輯)
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院國(guó)家金融與發(fā)展實(shí)驗(yàn)室設(shè)立于2005年,原名“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院金融實(shí)驗(yàn)室”。這是中國(guó)第一個(gè)兼跨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和自然科學(xué)的國(guó)家級(jí)金融智庫(kù)。2015年6月,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庫(kù)型研究機(jī)構(gòu)的基礎(chǔ)上,更名為“國(guó)家金融與發(fā)展實(shí)驗(yàn)室”。2015年11月,被中國(guó)政府批準(zhǔn)為首批25家國(guó)家高端智庫(kù)之一。
本公眾號(hào)獨(dú)家文章未經(jīng)授權(quán)不得以任何形式轉(zhuǎn)載、摘編。如若轉(zhuǎn)載,請(qǐng)聯(lián)系我們,并注明來(lái)源,文章標(biāo)題文字和內(nèi)文文字(包含文末責(zé)任編輯)禁止二改!否則一經(jīng)發(fā)現(xiàn),將追究相關(guān)責(zé)任,謝謝理解和配合。以上就是關(guān)于pos機(jī)運(yùn)行成本,支付工具的社會(huì)成本估算的知識(shí),后面我們會(huì)繼續(xù)為大家整理關(guān)于pos機(jī)運(yùn)行成本的知識(shí),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!